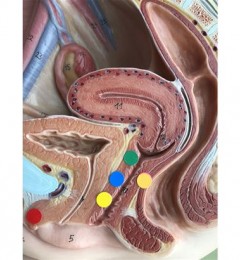9月8日,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公布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获奖人名单。李家洋、袁隆平、张启发摘得“生命科学奖”,马大为、冯小明、周其林获得“物质科学奖”,林本坚荣膺“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未来科学大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科学委员会首届轮值主席丁洪介绍,未来科学大奖关注原创性的基础科学领域研究,奖励为大中华区科学发展做出杰出科技成果的科学家(不限国籍)。
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作为科学委员会委员的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何川谈到,近年来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科学研究,为科研创新不懈努力。他表示,未来科学大奖既是对科研工作者所取得成果的肯定,也必将为未来出现更多振奋人心的科研成就提供巨大的助推力。

芝加哥大学官网何川教授介绍页
何川教授198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200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000-2002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10年7月,晋升为芝加哥大学正教授。2013年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HHMI)研究员。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教授、生物物理动态研究所主任,兼任北京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我们也采访了作为“未来科学大奖”评审的何川教授,他为我们揭露了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奖背后的故事,并讲述了他个人的科研经历和关键节点的选择。
问:何老师好,作为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委,能问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的呢?
何川:一开始的时候,是国内的一些科研工作者、科学家有了这个想法,后来可能想在化学方面,同时也在生命科学方面,能找一个人加入进来,然后就找到了我。因为我化学也做、生命科学也做,所以大概比较合适吧。
我觉得首先能和这么一些科学家在一起做这件事我自己也觉得挺高兴的;第二点,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虽然大家都很忙,但都带着一种使命感,很敬业地完成这件事情。
问:大牛云集的评委团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呢,在评审过程中会发生激烈的讨论吗?
何川:我觉得,首先大家都是在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对科研有自己的见解,然后对真正优秀的工作有很高的鉴赏力。因为他们自己做过第一流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评价体系里头能够分清楚哪一些是真正超一流的成果。
至于激烈的讨论嘛,这点我想,所有的评奖可能都会有的,因为大家不可能对每一件事都有同样的看法的。我想评奖的这些委员会的委员,别的不说,独立的思考能力都很强。所以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么我想就是说争论啊,一些不同的想法呀,一些意见啊,这是肯定会有的。
问:整个评奖过程会是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何川:像所有的大奖它都会经过很多轮的讨论。从一开始,委员会发了好几百份提名邀请信,到提名,到对这些题名的候选人进行筛选、评估,到讨论,到最后投票,这还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的。在整个过程中,评奖的时候只有九个科学家,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九个人在讨论,所有的募捐人也好,秘书处也好,都不会参与评奖的任何一点的。连结果评出来之后,除了评委团的九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整个这个名单确定下来之后,秘书处才知道,然后才开始安排,那也是最后一天的事儿。所以还付出了挺多工作的,他们在国内的付出的时间比我们多多了。
问:传统观念里,对科学家会有一种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的刻板印象。未来科技大奖的高奖金、高荣誉,是对这种传统的观念的冲击吗?
何川:呃,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虽然是高奖金,但是可能对这些获奖的科学家,从钱上的意义并没有从名誉上的意义那么大。我想首先要感谢企业家们提供了奖金,他们做这件事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目的,就是想回报社会吧。
如果你真的去看看科学家付出的,看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跟他金钱上所得的回报,是不成比例的。做科学的人,他并不奢求这个,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把奖金提到一个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地步。我希望这也产生一个效应,我们希望激励年轻人,青年一代,投身到科学研究里来。
问:是的,近年来也有很多社会的讨论,越来越少的年青人愿意走科研的道路,您是觉得你们的奖项是为了扶正这种错误的社会风气吗?
何川:其实我觉得最可能是主要的目的吧。最早的几位,尤其是几位企业家,还有一开始的几位科学家,秘书处都有这个想法。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都是八十年代在学校里面,有些七十年代末在学校里面。那个时候这个社会比较崇尚知识和科学,现在的社会可能在这方面,在科研这个方向,相对来讲对年轻一代吸引力没那么强了。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它需要发展各个方向,经济、法律、金融,每个方向都要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研的创新能力还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一个主要基石,如果在这个方面上落后的话,这个国家挺难真正在科技上,在整个生产力上全方面建立成一个真正的强大的国家。
我想可能从这个着眼点,很多人想做一些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一代投身到科研创新里面去。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目的,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唤起大家对科学的兴趣吧,就是提高社会的整体科学素养,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科学家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觉得这件事有意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问:最近这几年中国发展的非常快,比如说像未来科学大奖就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我知道您的经历中,您得到的是有一个重要的荣誉是得到HMMI的investigator,这种机制不只是一种荣誉,也是对你的科研有一定的资助,给了一定的宽松的环境。你觉得中国有没有希望引入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机制会不会对青年学者,或者对科学的发展有什么好处?
何川: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特别的好,如果看美国的话,其实,在现在美国科研经费的竞争压力也非常大。而Hughes、HMMI它这么多年来做得很成功,因为它资助人,它给你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去做有意义的工作。很多工作在你开始做的时候,只是一个好奇心,它的很多impact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每当你有真正的新的发现的时候,它的impact最终都会显现出来。我自己是一个Believer of Basic Research,做基础研究,正如HHMI需要你做innovative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工作。他主要看几点,第一点,你得有你自己的identity,你是谁,你做的东西和别人得不一样。这点我觉得中国有关机构可以借鉴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的PI还是挺忙于四处去申请项目,做预算等等。像Hughes他给你一笔钱,给你足够的自由度做你想做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一个机制在中国的话,它的那个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比现在的那些机制要有效率很多很多。我觉得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像王晓东老师办的NIBS一开始也很像那种机制,每个年轻PI进来之后有一笔固定的经费,然后你做你喜欢做的,但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一个全国性的机制,我想会很有效率。
问:那您当初是怎么选择科研这条道路的呢?
何川:我们这一代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成绩最好的基本上都觉得自己应该去做科研、做科学家,当时大家都理想主义吧,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吧。大家都觉得,献身科学挺伟大崇高的,大家都有理想,有追求。但我是在博士毕业之后,犹豫了一下,开始做博士后了,那就肯定已经下定决心接下来可能要争取做教授(走上科研这条道路)。
问:您职业生涯一个转折点就是从化学领域,转到生物领域,能问一下您做出这个决定的前因后果吗?
何川:呃,这个决定可能对我来讲,是比较完美,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因为化学里也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一开始在PhD的时候做化学,了解一些生物相关的背景,在博士后的时候做了些生命科学方面的工作,后来开始做助理教授的时候,也做些biochemistry。然后我后来拿到终生教授的时候,觉得我得做点儿新的东西了。当时我觉得在生命领域,未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不像别的学科,像化学、物理、数学经历了这么多年,在很多方向都已经发展的挺不错的了。当时是基于这个想法,然后把我自己的化学的那块儿给关掉了,完全集中在生命上面。在生命上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其实从biochemistry、structural biology、DNA repair、microbiology一路做过来。我一开始做DNA repair,也做pathogen research,也做structural biology,也做一些metallprotein,一直在摸索哪个方向自己能够真正的有自己的identity。当然最后做到epigenetics,然后做到RNA methylation上,觉得才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这也是一个过程。
问:那您在这寻找过程中,会有迷茫的时候吗?
何川:额……每个星期都很迷茫(哈哈哈)。当然,现在做得很开心,因为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是我们自己开辟的,然后别人都认可,很多人也都在做,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发现在基本生命过程,和绝大多数生命科学领域都有很大的impact,做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问:但是工作做出来之前您就知道会有impact吗?
何川:当然,一开始的选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点其实我们实验室做的还不是太好。我觉得在选题上,首先这个课题的方向是不是有biological importance,这是最重要的,做出来后它有没有significance。这个有时也看不清,也是一个科研的过程吧,如果每一个项目都成功的话,那科研可能也就没有这么有魅力了。
问:卢教授在完成他的工作后,又在二代测序的发展之下然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也惠及我们普通人。然后在表观领域我觉得是测序技术发展的比较快的一个领域,也是比较受益于测序技术发展的一个领域,然后现在也开发了很多方法。你觉得这么多方法,就是为以后未来的研究能带来什么样的突破方向呢?
何川: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的,因为表观遗传学是在现代的生物学里头几乎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里去了,在表观遗传学上发展的这些测序的技术,现在也五花八门,但是我觉得真正按科研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像单细胞呀,高精度的测序,不管它是histone mark也好,DNA methylation也好,离理想的技术还是有差距的。然后你要是把它做到临床上去,不仅要有这种高精度、单细胞什么的,你同时还得做的相对比较便宜,robust,我觉得还是有不少挑战的。有挑战也证明有很多机会,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问:像您自己也开发了很多测序方法是吗?
何川:我们实验室始终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做basic science,RNA methylation,这上面有很多很多science,我们要做,当然没有新的方法的话,你的science有时候也推动不了。所以我们在RNA methylation上本身我们现在也开始发展各种各样的测序方法。我们另一块呢,我的实验室主要在DNA甲基化,羟甲基化上做大量方法的改进、发明和应用。因为表观遗传学涉及到了几乎生命科学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方法出来之后,它可以促进新的生物学机制的发现,同时也可以有可能有很大的社会效益,比如临床检测。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信条,这也是以前我一个很好的前辈朋友跟我说的,“你做事要么这个东西真的有fundamental importance,能写到textbook里头,要么你这个东西就有很广阔的应用价值,可以摆到货架上去卖。”我觉得这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一个方法发明出来,每个人都愿意用,这也是它的价值的体现。